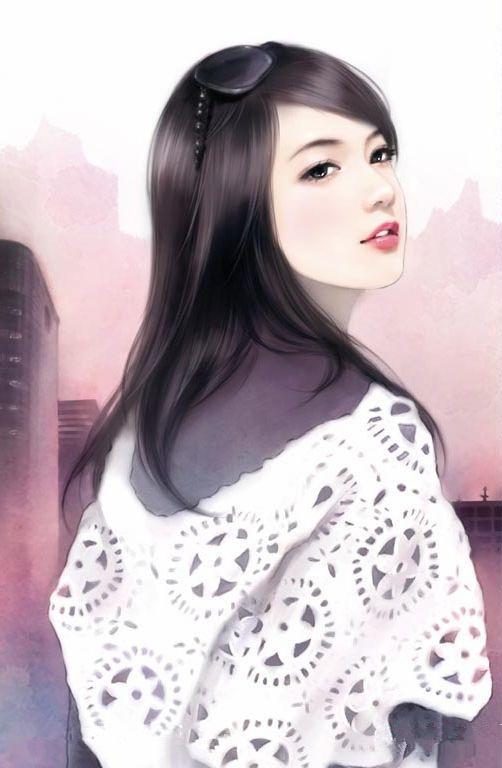五六小说>狐妖:容我三思 > 第119章 忠二(第1页)
第119章 忠二(第1页)
“什么?!!”
母亲赵秀芹失声惊呼,那声音尖锐得几乎要刺破屋顶,她手中的筷子“啪嗒”一声掉在粗糙的木桌面上,又滚落在地,她也顾不上去捡,脸色在油灯昏黄的光线下瞬间变得惨白如纸,
“俊儿!你……你糊涂啊!你为什么要去报名?那沧盐州……娘听人说起过,之前又是闹妖祸,又是各方争夺,乱得很,听说死过不少人!多危险的地方啊!咱们家在涂山,不是安安稳稳的吗?你这才刚适应了军营……为什么非要往那险地里去?你……”
她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哭腔,语无伦次,充满了母亲对儿子安危最本能的恐惧。
“闭嘴!先听俊儿把话说完!”
父亲魏铁山猛地呵斥了一声,打断了妻子那带着绝望意味的追问。他的脸色也同样凝重得如同铁铸,胸膛不受控制地微微起伏着,显示出他内心同样激烈的震荡,但他凭借着一家之主的定力,强行控制住了几乎要溢出的情绪,只是用那双看透了半生悲欢离合、世态炎凉的眼睛,紧紧攫住儿子的目光,仿佛要从中读出他真正的想法。
同时,他转向被这紧张气氛吓得有些呆住的小儿子,语气不容置疑,带着前所未有的严厉:
“狗娃,听话,去里屋自己玩会儿,爹娘跟你哥有要紧事说。”
小弟弟魏狗娃看着父亲从未有过的严肃表情,又看了看母亲泪光闪烁的眼睛和二哥紧绷的脸,虽然满心不情愿和好奇,还是瘪了瘪嘴,不敢违拗,一步三回头地、慢吞吞地挪进了光线更暗的里屋。
屋内顿时只剩下三人,空气仿佛凝固成了沉重的冰块,压得人喘不过气。只有桌上那盏小油灯的火苗,还在不安地跳动着,将三人的影子在墙壁上拉得忽长忽短,扭曲晃动。
魏仁俊看着父母,尤其是母亲那泫然欲泣、几乎要崩溃的样子,喉头艰难地滚动了一下,一股酸涩涌上鼻腔。
但他知道,此刻绝不能软弱。他深吸一口气,继续说了下去,声音比刚才更加低沉,却也更具有穿透力:
“爹,娘,你们应该还记得,时常跟我说起……咱们家,原本……并不是涂山的。”
他这句话,像是一把生锈却依旧锋利的钥匙,猝不及防地打开了那扇尘封着痛苦与颠沛流离记忆的大门。
父亲魏铁山的嘴唇紧紧抿成了一条坚硬的直线,下颌骨的线条绷得紧紧的。母亲赵秀芹的眼圈瞬间红透,泪水终于忍不住,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,她用粗糙的手背徒劳地擦拭着。
“咱们是从北地州,被那些黑了心肝的地主豪强,勾结官府,夺了田,占了屋,逼得实在活不下去了,才不得不背井离乡,像丧家之犬一样,一路乞讨、躲藏,历经千辛万苦,才逃难来的涂山。”
魏仁俊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、对过往苦难的哽咽,更有一种对不公世道的愤懑,“爷爷奶奶的坟茔,听说……还在北地州老家那边的荒山坡上吧?这么多年了,风吹雨打,我们这些不肖子孙,连一炷香、一张纸钱都没能去坟前烧过。还有外公外婆……我从小就没见过他们的面,只听娘在夜深人静时,偷偷抹着眼泪提起过……”
他的目光变得悠远而深邃,仿佛穿透了这间简陋木屋的墙壁,跨越了千山万水,看到了那片遥远、陌生却又承载着家族血泪的故土:
“我们这次离开涂山,远赴沧盐州,绝不仅仅是为了执行一道冰冷的军令,去一个陌生的地方。辅大人不止一次对我们说过,我们北府军要做的,是去改变!是去亲手打破、去改变那种逼得无数像咱们家一样的普通人家背井离乡、有家不能回、有亲不能祭的吃人世道!是去改变那种让咱们这样的升斗小民,永远被权贵踩在脚下、永无出头之日的途径!”
他越说越激动,年轻的脸庞在跳跃的油灯光下泛着一种近乎神圣的光辉,那是理想与信念的光芒:
“爹!娘!儿子这次报名,不单单是为了服从军令,更是为了咱们魏家,为了像咱们家一样,受过太多苦、流过太多泪的千千万万个家!儿子想用自己的这双手,这把刀,去拼杀,去搏一个不一样的将来!”
“为了有一天,咱们魏家的后人,能堂堂正正地、光明正大地回到故土,去给爷爷奶奶,还有外公外婆,好好地磕几个头,恭恭敬敬地上一炷香!告诉他们,他们的后人,再也不用像你们当年那样,被人像驱赶牲口一样,毫无尊严地四处逃亡了!我们要的,是一个能让所有人都能安身立命、不再受欺凌的世道!”
一番话,如同道道惊雷,接二连三地炸响在这小小的、昏暗的木屋之内,震得梁上的灰尘似乎都簌簌落下。
母亲赵秀芹再也忍不住,用手死死捂住嘴巴,可那压抑不住的、破碎的哭声还是如同决堤的洪水般从指缝里汹涌而出,她瘦弱的肩膀剧烈地颤抖着,眼泪如同盛夏的暴雨,滚滚而下,瞬间打湿了她粗糙的衣襟。
小主,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,后面更精彩!
父亲魏铁山的身体也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起来,他猛地别过头去,不想让儿子看到自己此刻的表情,用那双布满厚厚老茧和无数裂口的大手,狠狠地在脸上抹了一把,试图擦去那不受控制涌出的温热液体。当他再转回头时,眼圈是通红的,鼻翼也因为强忍情绪而微微翕动着。
他看着儿子,看着这个在自己眼皮底下一天天长大、如今已然羽翼渐丰、有了远自己想象的抱负和担当的儿子,千言万语,无数的担忧、不舍、骄傲、复杂难言的情绪,如同乱麻般堵在喉咙里,翻腾涌动,最终却只化作了一声长长的、仿佛耗尽了全身力气的、带着无尽沧桑与复杂情绪的叹息。那叹息声,在寂静的屋里显得格外沉重。